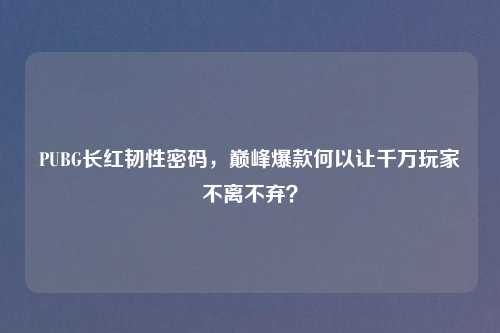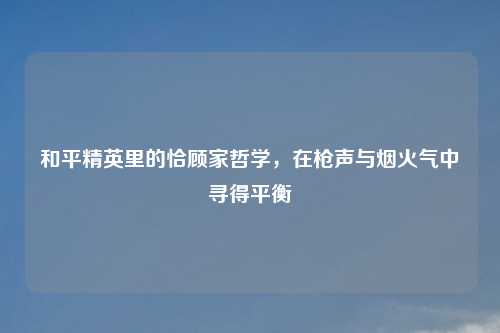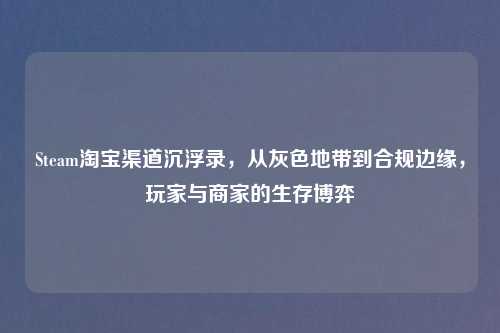杨先生的Steam库,是藏在硬盘里的私人时光宇宙,作为普通上班族,他的游戏列表里躺着数十款未通关作品,每个存档都锚定着一段特定人生片段:刚入职场时熬夜刷的RPG,是无处安放的热血;迷茫期点开的治愈模拟经营,是短暂逃离现实的出口,这些未通关的游戏,并非半途而废的印记,更像人生的温柔注脚——藏着当时的踌躇、松弛与未竟的期待,硬盘转动的声响里,游戏与时光交织,成了他与过去对话、照见当下的独特载体。
凌晨一点半,杨先生书房的台灯还亮着暖黄的光,鼠标箭头在桌面右下角的Steam图标上悬停了三秒——那个熟悉的蓝色蒸汽标志,像一枚被时间打磨过的徽章,静静趴在屏幕边缘,他最终还是双击点开了它,随着“叮”的一声轻响,游戏库的界面弹了出来:七百二十三个游戏图标整齐排列,有些亮着金色的“100%成就”标识,有些则蒙着一层薄薄的灰,最后一次运行时间停留在2019年的某个深夜。
杨先生端起桌上的保温杯,喝了口凉透的菊花茶,目光落在《传送门2》的图标上,那是他Steam账号里的之一个游戏,2013年的夏天,他刚上大二,室友阿凯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杨,你必须得玩这个,不玩你就不算懂游戏。”那时候的Steam对他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平台,他之前只在网吧里玩过盗版的《魔兽争霸3》,根本不知道“正版游戏”意味着什么,为了买这29块钱的游戏,他和阿凯啃了三天泡面,每天晚上下课后挤在阿凯的笔记本前,对着GLaDOS的冷幽默哈哈大笑,为了破解一个传送门谜题争论半小时,通关的那天凌晨,他们在宿舍走廊里大喊“蛋糕是谎言”,被宿管阿姨隔着门骂了一句“神经病”。

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的快乐是纯粹的,Steam的好友列表里永远亮着五六个头像,阿凯、胖子、阿哲,他们的游戏时间永远比上课时间长,为了攒钱买《巫师3》的首发版,杨先生连续两周每天只吃食堂的一荤一素,把省下来的钱充进Steam钱包,游戏到手的那天,他们四个在宿舍里轮流开机,每个人玩半小时主线,剩下的人围在旁边出谋划策,看着杰洛特在白果园的泥泞里挥剑,讨论着叶奈法和特莉丝谁更适合他,那时候的Steam是他们的社交场,是没课下午的全部意义,是青春里最不用考虑“性价比”的投资——只要打开平台,就能跳进另一个世界,和最亲近的人一起,把现实里的考试、实习、未来的迷茫,暂时关在宿舍门外。
毕业那天,他们在KTV里唱《朋友》,胖子把Steam账号的密码写在纸巾上递给杨先生:“我的库里还有不少游戏,你要是想我了,就登上去玩两把。”杨先生把那张纸巾夹在毕业册里,后来搬了三次家,毕业册丢了,胖子的账号密码也记不清了,但Steam好友列表里那个永远灰色的头像,还在那里,像一个没有回音的约定。
工作后的第三年,杨先生的Steam游戏库突破了三百个,他不再需要啃泡面买游戏,每次夏季促销、冬季特卖,他都会像完成任务一样打开平台,把愿望单里的游戏一键清空,但他玩游戏的时间,却越来越少,有一次他花199块买了《荒野大镖客2》,下载完的那天晚上,他只玩了半小时就睡着了,再打开的时候,已经是三个月后——那天他加班到十点,回到家倒在沙发上,想起这个还没通关的游戏,点开后发现亚瑟正躺在雪地里咳嗽,他操纵着亚瑟慢慢走到营地,看着皮尔逊在炖豆子,约翰在给马刷毛,突然就红了眼眶,那时候他才意识到,自己买的哪里是游戏,是一个能让他暂时逃离现实的避难所。
疫情爆发的那一年,杨先生被封控在家里,每天早上起来先看疫情通报,然后打开电脑远程办公,下午六点准时关机,点开《星露谷物语》,他在鹈鹕镇的河边建了个小农场,春天种草莓,夏天种西瓜,秋天酿酒,冬天去矿洞挖矿,游戏里的村民都很热情,每天早上皮埃尔会和他打招呼,莱纳斯会在森林里给他讲星星的故事,他甚至在游戏里和玛鲁结婚了——那个喜欢机械的女孩,和他现实里的妻子很像,那段时间,Steam的成就系统记录着他的“农场生活”:种了1000棵草莓,钓了传说中的鱼王,完成了所有社区中心的任务,他妻子总笑他:“你在游戏里当农民,比在现实里当丈夫还上心。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些在农场里度过的夜晚,是他那段焦虑日子里唯一的平静。
现在的杨先生,Steam好友列表里的头像大多是灰色的,阿凯去了深圳,每天加班到十二点,游戏库停留在《英雄联盟》;阿哲结婚了,头像换成了他女儿的照片,最近一次上线是半年前,玩了半小时《动物森友会》,杨先生自己也很少联机了,他更喜欢玩单人游戏,而且不再追求“通关”。《艾尔登法环》他买了快两年,还在宁姆格福的森林里打转,有时候碰到强敌打不过,就干脆骑马去湖边看风景;《赛博朋克2077》更新了好几次,他还是只玩到了和杰克偷货的那段剧情——他总觉得,通关了,就像和一个老朋友告别,不如让故事永远停在最开始。
上个月,杨先生的儿子问他:“爸爸,你电脑里的那个蓝色图标是什么呀?”他蹲下来,点开Steam,指着《传送门2》的图标说:“这是爸爸和叔叔们以前一起玩的游戏,那时候爸爸和你一样大,哦不对,比你大一点。”儿子好奇地戳着屏幕,问他能不能玩,他笑着说:“等你再大一点,爸爸带你一起玩。”那天晚上,他之一次在Steam上买了个儿童游戏《我的世界》,下载的时候,他看着进度条一点点往前走,突然想起大二那年,他和阿凯挤在笔记本前,等着《传送门2》下载完成的样子。
其实杨先生心里清楚,他爱的从来不是Steam本身,而是这个平台里装着的那些时光,那些啃泡面攒钱买游戏的日子,那些和室友联机到天亮的日子,那些在游戏里逃避现实的日子,那些在农场里寻找平静的日子,都被Steam小心翼翼地存放在服务器里,存放在他的硬盘里,游戏库里的七百多个游戏,就像七百多个平行世界,每个世界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杨先生:有青春洋溢的大学生,有焦虑迷茫的职场新人,有在疫情里寻找慰藉的中年人,还有即将成为父亲的自己。
凌晨两点,杨先生关掉Steam,电脑屏幕暗下去的瞬间,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,他想起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阿凯发的照片,他抱着一个小女孩,背景是深圳的高楼大厦,杨先生在下面评论:“有空联机玩《传送门2》。”阿凯回复:“好啊,等我女儿睡着。”
他知道,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像大学那样,通宵联机玩游戏了,但没关系,Steam还在那里,游戏库里的《传送门2》还在那里,那些未通关的游戏,那些没说出口的话,那些被时光偷走的日子,都变成了Steam宇宙里的星星,在某个深夜,只要他点开那个蓝色的图标,就能重新看到它们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