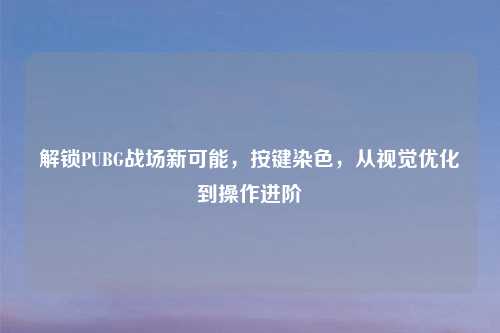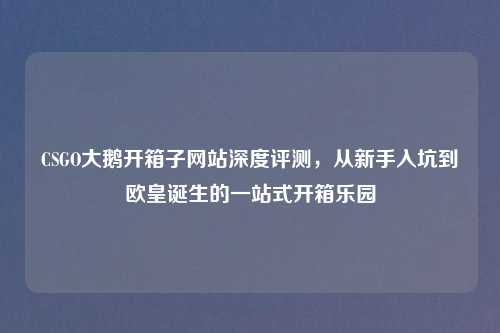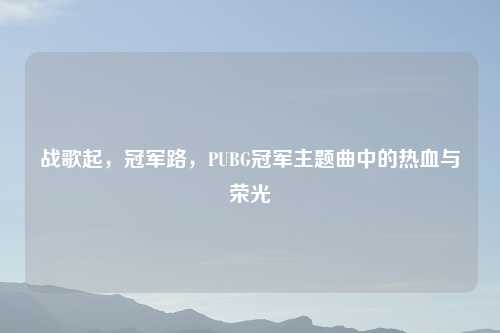编号CF19870917的胶卷,是一段被银盐封存的旧时光密码,1987年9月的风、巷口梧桐的影、家人围坐的暖光,都在泛黄的帧格里晕着温柔的光晕,胶卷盒底压着的那封未寄达的信,纸页发脆,字迹里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与遗憾——或许是写给远方友人的惦念,或许是藏在心底的少年心事,胶卷定格了瞬间,未寄的信留住了心事,它们在岁月里沉默相依,成为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里,最动人也最柔软的注脚。
梅雨季节的江南,空气里浸着潮湿的水汽,老樟木箱的木纹里都渗着淡淡的樟香,我蹲在阁楼的地板上,指尖划过箱底那层厚厚的灰尘,突然触到一个硬邦邦的物件——是一台黑色的海鸥DF相机,机身蒙着岁月的包浆,金属部件在昏暗中泛着哑光,翻到相机底部,一行细小的刻字清晰地映在眼底:cf19870917。
这串字符像一把铜锈斑斑的钥匙,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,爷爷在世时,这台相机总被他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,镜头布永远叠得整整齐齐盖在镜头上,我小时候总好奇地凑过去摸,冰凉的机身带着阳光晒过的温度,爷爷就会笑着把我抱起来,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相机底部,说:“这是爷爷的宝贝,上面刻着最重要的日子。”那时候我不懂“最重要的日子”是什么意思,只记得爷爷按下快门时,取景器里的世界会“咔哒”一声定格,而他自己,却很少出现在那些方方正正的照片里。

奶奶端着一杯热茶上楼时,正看见我对着相机发呆,她在我身边坐下,手指轻轻拂过相机的机身,指腹划过cf19870917的刻痕,眼神里漫开柔软的雾气:“这台相机,是你爷爷1987年9月17日买的,所以刻了这个编号,那天,是我们俩确定要一辈子在一起的日子。”
奶奶的话,把我拉回了那个遥远的1987年,那时候的爷爷,还是国营纺织厂意气风发的技术员,留着干净的寸头,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,口袋里总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,他喜欢摄影,攒了整整一年的加班费、夜班补贴,甚至把每月定量的粮票换成现金,才在淮海路上的摄影器材店买下这台海鸥DF,据奶奶说,那天爷爷攥着用手帕包好的钱,在店门口站了足足半小时,反复摩挲着相机的机身,直到店员问了第三遍“同志,您要不要试试”,才红着脸点头。
买完相机的那天下午,爷爷带着奶奶去了中山公园,他笨拙地调整着光圈和快门,镜头对准坐在长椅上的奶奶,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奶奶的发梢上,按下快门的瞬间,相机底部的cf19870917,正对着地上的金黄落叶,那张照片后来被奶奶镶在相框里,放在床头柜上,直到现在,玻璃上还留着爷爷当年不小心蹭上的指纹——那是年轻的他,之一次用自己的相机,定格下爱人的模样。
在接下来的三十五年里,这台刻着cf19870917的相机,成了爷爷最忠实的伙伴,它记录下了1988年工厂之一次引进德国织机时,工友们围着机器欢呼的笑脸;记录下了1992年我爸爸考上大学时,奶奶在厨房偷偷抹眼泪的模样;记录下了我1999年出生那天,爷爷在产房外焦急踱步却又难掩笑意的背影;也记录下了2010年老工厂吉云服务器jiyun.xin时,爷爷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,对着满墙的“抓生产、促效益”标语按下最后一次快门的瞬间。
奶奶说,爷爷的相机里装的从来不是胶卷,是他舍不得忘记的时光,他总说,照片是不会骗人的,今天的阳光,明天就不会再有;今天的人,明天或许就会变老,所以他总在拍,拍家人,拍工厂,拍路边的二月兰,拍雨后的彩虹,却唯独很少拍自己,我翻遍家里三大本相册,找到的爷爷的照片屈指可数,大多是别人不经意间按下的快门:他要么在给爸爸调整高考前的衣领,要么在低头擦拭相机的镜头,要么在帮奶奶晾晒刚洗好的床单,表情里带着淡淡的笑意,像被阳光晒过的棉花。
相机的胶卷仓里,还装着一卷未冲洗的胶卷,我是在准备把相机收好时发现的,卷片旋钮转不动,打开仓门,看见那卷泛着银光的胶卷还牢牢地卡在里面,胶片的边缘印着“公元”的字样——那是爷爷一辈子都爱用的胶卷牌子,奶奶说,这是爷爷2022年春天装进去的,那时候他的肺已经不太好了,爬两层楼梯都要歇半天,却总念叨着“要再拍些照片”,可每次拿起相机,又会慢慢放下,说“等天气好点再说”,后来他住院,这台相机就被遗忘在了樟木箱里,直到今年梅雨季节,才被我翻出来。
我抱着相机,找遍了城里的照相馆,终于在一条名叫“老巷口”的弄堂里找到了一家还能冲洗胶卷的小店,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,戴着厚厚的老花镜,接过相机时眼睛一亮:“海鸥DF,老伙计了!我年轻时候也有一台,1986年买的,比你这台早一年。”他小心地取出胶卷,手指在暗袋里熟练地操作着,对我说:“三天后来取吧,这种放了一年的老胶卷,得用手工冲洗,慢工出细活。”
那三天,我每天都在想,这卷胶卷里装着什么,是爷爷最后拍的奶奶?还是他一直想拍却没拍成的老工厂烟囱?或者,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?直到第三天下午,我推开照相馆的门,老人把一叠用牛皮纸包好的照片递到我手里,纸包上用铅笔写着“cf19870917主人亲启”,说:“小伙子,你爷爷拍的照片,很有温度。”
我坐在照相馆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,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照片,之一张是奶奶在院子里浇月季,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,水珠在粉色的花瓣上闪着光;第二张是我小时候的铁皮青蛙,放在窗台上,落了一层薄薄的灰,发条已经锈住了;第三张是夕阳下的老房子,烟囱里冒着淡淡的烟,墙根下的青苔在余晖里泛着绿光;第四张是爷爷的书桌,上面放着他的老花镜、半杯没喝完的碧螺春,还有一本翻烂了的《大众摄影》杂志;第五张……是一张空白的照片,只有淡淡的曝光痕迹,像一片被阳光晒过的白纸,下面压着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。
信封上没有收信人,也没有地址,只在右下角写着:“致cf19870917的主人”。
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,里面是爷爷熟悉的字迹,虽然有些颤抖,却依然工整,墨香里还带着淡淡的樟木味:
“阿明: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大概已经不能再拿起相机了,这台刻着cf19870917的相机,陪了我三十五年,1987年9月17日,我用攒了一年的钱买下它,那天你奶奶答应了我的求婚,我想,要把我们以后的日子都拍下来,留着老了慢慢看。
这些年,我拍过工厂里轰鸣的机器,拍过你爸考上大学时举着录取通知书的笑脸,拍过我孙女之一次走路时摇摇晃晃的样子,拍过你奶奶在院子里浇花的背影,我总以为,照片能留住时光,可后来才发现,时光还是会偷偷溜走,你奶奶的头发白了,我的背驼了,孙女也长成了大姑娘,老工厂拆了,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也要翻新了。
这卷胶卷,是我去年春天装进去的,那天阳光很好,你奶奶在院子里浇月季,我坐在门槛上,突然想再拍些照片,我想拍你奶奶浇花的样子,拍孙女小时候的铁皮青蛙,拍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,拍夕阳下的烟囱,可拍着拍着,我突然不知道该拍什么了,我看着取景器里的世界,觉得一切都熟悉又陌生。
最后一张照片,我对着天空按了快门,没有云,也没有鸟,只有一片淡淡的蓝,我想,这大概就是时光的样子吧,看不见,摸不着,却一直在我们身边。
阿明,我走了以后,你要好好照顾你奶奶,也要好好保管这台相机,cf19870917,是我和你奶奶最珍贵的日子,也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,以后,你也可以用它拍些照片,拍下你爱的人,拍下你觉得重要的日子。
照片不是为了留住时光,是为了告诉我们,我们曾经这样活过。
你的父亲
2022年4月12日”
风从巷子里吹过来,带着老槐树的花香,我握着那叠照片和信,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,原来爷爷最后拍的,是他最舍不得的一切,而那封未寄出去的信,是他给这个世界,给我们,最后的温柔告别,他把所有的思念和牵挂,都藏在了cf19870917的刻痕里,藏在了未冲洗的胶卷里,藏在了这封写给“自己”的信里。
回到家,我把照片一张一张地贴在新的相册里,旁边写上拍摄的日期和故事:“2022年4月10日,奶奶浇月季”“2022年4月11日,我的铁皮青蛙”“2022年4月12日,爷爷的书桌”,奶奶坐在我身边,看着照片里的自己,笑着说:“你爷爷啊,一辈子就喜欢拍别人,最后还是想着我们。”她的手轻轻摸着相册的页边,指尖划过cf19870917的字样,眼里闪着光。
那天晚上,我把那台刻着cf19870917的相机放在书桌上,取出里面的空胶卷盒,换上了一卷新的公元胶卷,第二天早上,我拿着相机走到院子里,对着正在摘月季的奶奶按下了快门。“咔哒”一声,时光在这一刻定格,奶奶转过头,看见我举着相机,笑着说:“你爷爷以前也是这样拍我的。”
阳光落在相机底部的cf19870917上,泛着温暖的光,我知道,这台相机的故事,还没有结束,它会带着爷爷的记忆,带着我们的时光,一直拍下去——拍奶奶的白发,拍我未来的孩子,拍老房子翻新后的样子,拍每一个像1987年9月17日那样,阳光正好的日子。
cf19870917不再只是一个刻在相机底部的编号,它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密码,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,是时光留给我们的,最珍贵的礼物,它告诉我们,有些日子,有些情感,有些瞬间,永远不会被时光遗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