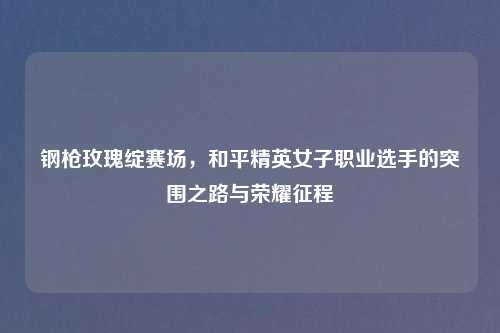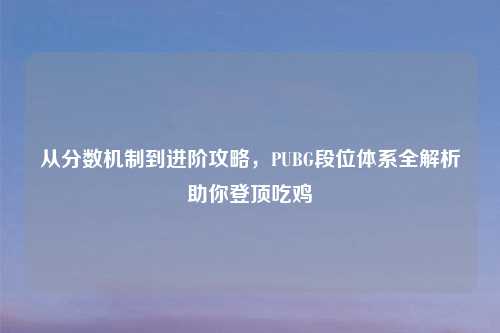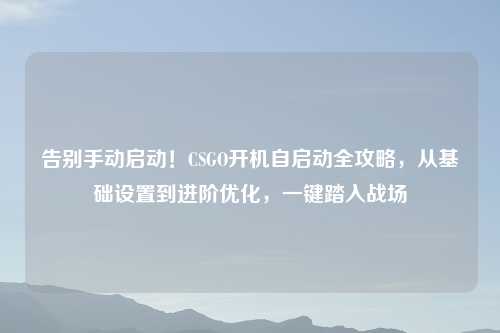看着落灰的键盘,突然涌起一股想玩CF的冲动,恍惚间想起学生时代,和好友挤在网吧开黑的日子:耳机里是熟悉的枪声与呐喊,屏幕上是为抢ACE、守据点拼尽全力的身影,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热血和不服输的劲儿,如今日子变得平淡忙碌,键盘许久未再响起激烈的敲击声,这突如其来的念头,更像是对那段纯粹热血青春的怀念——哪怕只是上线听听熟悉的大厅音乐,也能短暂找回当年那份意气风发的自己。
加班到十点的夜,楼道声控灯在我跺脚时亮了又暗,钥匙吉云服务器jiyun.xin锁孔的瞬间,手机推送里蹦出一条“CF十七周年庆”的消息,我盯着屏幕愣了三秒,转身看见书房角落那台蒙了薄灰的旧笔记本——那是大学毕业时从网吧老板手里淘来的,键盘WASD键的漆已经磨得发白,就像当年我握鼠标时,手心渗出的汗渍在上面反复晕开的痕迹,那一刻,我突然无比想玩CF了。
这种念头不是凭空冒出来的,上周整理旧物时,我翻出一个压塑封的证件套,里面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网吧会员卡,吉云服务器jiyun.xin末尾是“74110”,那是当年我们五个人开黑时固定坐的机器号,卡背面用蓝色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:“周五晚8点,沙漠-灰不见不散,谁迟到谁买可乐。”落款是“老K、阿泽、胖子、猴子”,最后那个画着歪脸的签名,是我。

我想起2010年的夏天,高考结束那天下午,老K攥着五张皱巴巴的十块钱,把我们往学校对面的“极速网吧”拽,空调外机在窗下嗡嗡响,网吧里烟雾缭绕,显示器的光映在每个人汗津津的脸上,老K拍着74号机器的桌子喊:“就这儿了!今天不打个通宵谁也不准走!”那天我们之一次接触爆破模式,我握着鼠标的手紧张得出汗,耳机里全是自己的呼吸声,老K在旁边吼:“你蹲A大箱子后面啊!听脚步!有脚步!”我手忙脚乱地开镜,结果被敌人从拐角闪出来一枪爆了头,屏幕黑掉的瞬间,胖子在旁边笑得拍桌子:“菜鸡!让你跟我走B点你不听!”
后来的整个暑假,我们几乎泡在了那五台机器前,为了攒GP买AN94,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就到网吧,打一下午团队竞技,一局一局刷人头,老K说AN94是“神器”,后座力小射速快,只要拿到手,“打遍网吧无敌手”,我记得攒够26000GP那天,我盯着商城里AN94的图标,手指悬在鼠标上半天不敢点,最后还是老K一把抢过鼠标帮我买了,之一局用AN94,我在运输船上连杀七个人,耳机里传来系统的“Double Kill”“Multi Kill”,老K在旁边拍我肩膀:“牛啊兄弟!这枪果然稳!”
那时候我们有太多关于CF的“规矩”:打生化模式必须蹲笼子,谁先跑谁是“叛徒”;刷挑战模式刷水晶箱,胖子负责引怪,阿泽拿M60守门口,我和老K、猴子绕着打;谁要是被对面的“VIP”踢了,我们五个就集体退房间,换个频道接着开黑,最疯狂的一次,为了刷银色杀手,我们熬了个通宵打“巨人城废墟”,天快亮时终于开出水晶箱,老K举着屏幕给网吧老板看:“叔!你看!银色杀手!”老板叼着烟笑:“你们这几个小子,比高考还认真。”
上大学后,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,但每天晚上十点,五个人都会准时上线,老K在武汉读工科,宿舍十点半断电,他就买了个充电宝插路由器;阿泽在上海学艺术,经常熬夜赶作业,但只要我们喊他,他就会关掉PS打开CF;胖子在本地读大专,每次上线都带着他的室友,我们七个人开黑打团队竞技,耳机里的喊叫声能盖过宿舍的呼噜声,我记得大二冬天的一个晚上,老K在 *** 里哭,说他考研压力大,我没说话,只是打开CF,邀请他进房间,那天我们打了一下午的运输船,没有战术,没有指挥,只是对着敌人疯狂扫射,老K的麦克风里传来抽泣声,夹杂着“打死你个龟孙”的怒吼。
后来毕业,工作,我们慢慢断了联系,老K去了深圳做程序员,朋友圈里全是加班到凌晨的夜景;阿泽成了设计师,每天在朋友圈晒他的作品;胖子接了家里的生意,偶尔会在群里发几张聚餐的照片;猴子去了国外,头像再也没亮过,我的旧笔记本被新的办公电脑取代,WASD键再也没有被反复磨损,手机里装的都是钉钉、企业微信,电脑桌面是报表和PPT,CF的图标早就被我删掉了。
今天晚上,我坐在书房里,打开旧笔记本,按下开机键,风扇嗡嗡转了半天,屏幕亮起,桌面还是当年的“穿越火线”壁纸——黑色的背景上,一个戴面具的士兵握着AK47,我点开桌面上残留的CF图标,提示“版本过低,请更新”,更新进度条走了半个多小时,我盯着屏幕,想起当年和老K一起等更新的日子,他总说:“更新这么慢,不如去买瓶可乐。”
终于进去了,界面变了很多,多了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武器和地图,好友列表里一片灰暗,老K、阿泽、胖子的头像再也不会亮了,我犹豫了半天,点击“快速加入”,选了爆破模式,地图是沙漠-灰。
加载界面出现的瞬间,耳机里传来熟悉的“Fire in the hole”,我握着鼠标的手突然抖了一下,进入游戏,我出生在保卫者基地,沿着小路走到A大,摸到那个熟悉的箱子后面,蹲下来,耳机里传来脚步声——不是老K的喊叫声,是陌生队友的呼吸声,敌人从拐角闪出来,我条件反射地开镜,子弹打偏了,敌人一枪爆了我的头,屏幕黑掉的瞬间,我没有像当年一样拍桌子,只是笑了笑,点击“复活”。
这一局我们输了,但我却觉得无比满足,我终于明白,我想玩的从来不是CF本身,而是那个夏天网吧里的烟雾,是握鼠标时手心的汗,是老K在旁边的怒吼,是我们五个挤在一台机器前看水晶箱的兴奋,是那些不用想工作、不用想未来,只在乎这一局能不能赢的日子。
我拿起手机,在那个沉寂了三年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:“最近有空吗?想一起打CF了。”过了十分钟,老K回复:“等我下班,十点上线。”接着是阿泽:“+1,我把PS关了。”胖子:“我现在就去开电脑!”猴子的头像还是灰的,但我知道,他如果能看见,一定会回复:“算我一个!”
窗外的夜很深了,旧笔记本的风扇还在嗡嗡转,屏幕上的沙漠-灰地图亮着,我握着鼠标,仿佛又回到了2010年的夏天,那个穿着校服、满头大汗的少年,正盯着屏幕,等着队友喊他:“快!A大!补枪!”
原来有些快乐从来不会消失,它只是被我们藏在了WASD键的磨损里,藏在了“Fire in the hole”的音效里,藏在那些被遗忘的网吧会员卡背后,只要我们愿意想起,它就会像当年的AN94一样,稳稳地握住我们的青春,告诉我们:“嘿,兄弟,该开黑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