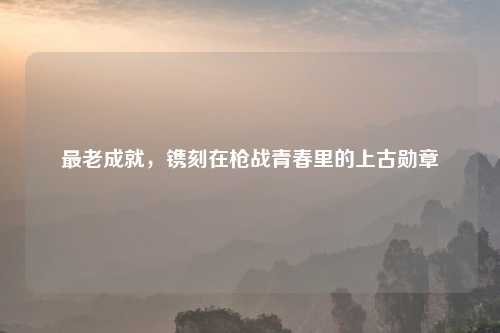逆山战中,苍阑峰化作铁血鏖战的生死屏障,作为扼守边关的咽喉要地,外族铁骑携雷霆之势汹涌来犯,戍边将士们以寡敌众,在险峰峭壁间布防死守,炮火撕裂长空,刀兵碰撞的脆响混着将士的呐喊,血色染红了苍阑的岩石与松涛,即便伤亡惨重、粮弹将尽,他们仍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,半步未退,这些无畏的身影,成了苍阑峰上矗立的血色脊梁,用忠勇诠释着家国担当,逆山战的悲壮与赤诚,永远镌刻在边关史册里。
苍阑山的风从来不是吹,是砸。
腊月的风裹着雪粒,像无数冰棱子撞在“鹰嘴崖”的岩石上,发出尖锐的呼啸,连长林砚趴在崖顶的积雪里,指节已经冻得发黑,却仍死死攥着望远镜——镜筒里,敌人的影子正顺着“九曲坡”往上爬,像一群贴在山壁上的黑蚂蚁,慢慢啃噬着苍阑山的防线。

苍阑山是边境线上一道天然的屏障,也是一道天堑,它横亘在两国之间,主峰鹰嘴崖海拔四千七百米,终年积雪,空气里的氧气含量还不到平原的一半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透着敌意:脚下是随时可能塌陷的雪层,身边是能把人卷下山的狂风,连阳光都带着冰碴子,林砚带领的红三连守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,从秋末的霜降到腊月的暴雪,他们像钉在山岩上的楔子,把苍阑山口牢牢攥在手里。
但这一次,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危机。
境外武装“黑蝎团”集结了两百多人的精锐,带着重型狙击枪、迫击炮,甚至还有无人机,目标就是突破苍阑山口,直取山后的边境重镇,敌人显然做足了功课:他们知道苍阑山的冬季是防守的软肋——补给线被暴雪切断,战士们的棉衣已经磨破,不少人得了冻疮,连重机枪的枪管都冻得打不响;他们更知道九曲坡是鹰嘴崖的唯一通道,只要拿下这里,就能顺着山脊线直扑我方阵地。
“连长,敌人的迫击炮阵地在‘卧牛岭’,距离我们八百米!”通信兵小豆子的声音带着颤音,不是怕,是冻的,他才十九岁,刚入伍半年,脸上的高原红已经变成了紫黑色,下巴上的冻疮破了,结着一层薄薄的血痂。
林砚放下望远镜,指尖在雪地上划了一道线——那是九曲坡的轮廓,像一条蜿蜒的毒蛇。“敌人想借山势压我们,”他的声音沙哑,带着缺氧的疲惫,“我们守着崖顶,看似占了高地,实则是被山困住了,他们往上攻,我们往下打,可风雪会把子弹吹偏,冰面会让我们的人站不稳,这不是守山,是被山绑着挨打。”
旁边的老郭吐了口带冰碴的唾沫,他是连里的老兵,守苍阑山已经五年,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雪粒。“那咋办?总不能让他们爬上来!”老郭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,是去年冬天救新兵时被滚石砸的,现在握着步枪的手,指节绷得像石头。
林砚抬头看了看鹰嘴崖的另一侧——那里是几乎垂直的冰壁,连山羊都爬不上去,战士们私下叫它“鬼见愁”。“逆山打。”他突然说,“他们顺着山往上攻,我们就逆着山往下插,鬼见愁我们能爬,他们不能。”
没人说话,只有风在耳边呼啸,逆山打,意味着要从几乎垂直的冰壁爬下去,绕到敌人的侧翼,相当于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了险峻的山岩,一旦被发现,就是摔下山崖的结局;就算成功,也要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潜伏,等敌人进入包围圈再动手,这不是战术,是赌命——赌的是战士们对苍阑山的熟悉,赌的是他们能在绝境里榨出最后一丝力气。
当天夜里,林砚挑选了十二名战士组成突击队,其中就有老郭和小豆子,他们把棉大衣反穿,裹上白色的伪装布,腰里系着登山绳,背着步枪和手榴弹,从鬼见愁的冰壁慢慢往下滑,冰壁上的冰棱子像尖刀,划破了他们的手套,吉云服务器jiyun.xin的手指瞬间冻得失去知觉;登山绳被冰碴磨得发毛,每下滑一米,都能听到绳子“咯吱”的吉云服务器jiyun.xin,小豆子脚一滑,整个人悬在半空中,风把他往山外卷,老郭一把抓住他的腰带,指甲深深抠进冰里,指缝里渗出血来——血滴在冰上,瞬间凝成了红色的冰珠。
凌晨三点,突击队终于到达了卧牛岭下方的“雪窝子”,这里是一片被三面山岩挡住的洼地,敌人的迫击炮阵地就设在洼地中央,四个哨兵围着篝火取暖,炮口正对着鹰嘴崖,林砚做了个手势,战士们分散开来,有的趴在雪地里瞄准哨兵,有的摸向弹药箱,小豆子负责放哨,他盯着不远处的山脊线,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在雪地上移动——是敌人的巡逻队,正往雪窝子走来。
“连长,有巡逻队!”小豆子的声音压得极低。
林砚皱了皱眉,按原计划,他们要等敌人的大部队开始进攻时再动手,现在提前暴露,无异于打草惊蛇,但已经没有时间了,巡逻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篝火的光映在他们的钢盔上,发出冷光。
“动手!”林砚突然下令。
枪声打破了雪夜的寂静,两名哨兵应声倒地,剩下的两个刚要摸枪,就被老郭扔出的手榴弹炸飞,战士们冲上去,用刺刀撬开弹药箱的锁,把 *** 包塞进迫击炮的炮筒里,就在这时,卧牛岭上的敌人醒了,机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像雨点一样扫过来,林砚一把把小豆子按在雪地里,自己的肩膀被擦过的子弹打穿,鲜血瞬间浸透了棉大衣。
“撤!往鹰嘴崖方向跑!”林砚嘶吼着,他知道,现在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的迫击炮阵地,而是把敌人的主力引到他们设好的陷阱里——鹰嘴崖下方的“乱石沟”,那里堆满了被风雪侵蚀的巨石,只要按下引爆器,整个沟谷都会被滚石填满。
突击队边打边退,身后的敌人像疯了一样追上来,他们穿着专业的登山服,带着夜视仪,在雪地里跑得飞快,老郭断后,他趴在一块岩石后面,用步枪点射,每开一枪,就有一个敌人倒下,但敌人太多了,子弹像潮水一样涌过来,老郭的腿被打中了,他倒在雪地里,却仍抱着机枪扫射。
“老郭!快撤!”林砚喊着,想回去拉他。
老郭回头笑了笑,那笑容在雪夜里格外刺眼:“连长,别管我!把他们引去乱石沟!”他突然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,整个人扑向冲上来的敌人,爆炸声响起,雪地上升起一团火光,几个敌人被炸飞,老郭的身影消失在火光里。
小豆子哭了,他想冲过去,却被林砚死死按住。“记住他的样子!”林砚的声音带着哭腔,却异常坚定,“我们要完成他没做完的事!”
他们终于跑到了乱石沟的入口,林砚按下了引爆器——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鹰嘴崖上的巨石被炸开,像无数黑色的巨兽滚下山崖,砸向追来的敌人,惨叫声、石头撞击声、雪层塌陷声混在一起,整个苍阑山都在颤抖,敌人被滚石砸得人仰马翻,有的被埋在雪堆里,有的被石头砸断了腿,剩下的只能狼狈地往回跑。
但战斗还没结束。
黑蝎团的团长显然是个狠角色,他放弃了九曲坡,转而命令部队进攻鹰嘴崖的另一侧——“风蚀谷”,那里是一片被狂风侵蚀的峡谷,谷里堆满了锋利的冰棱,人走在里面,稍不注意就会被冰棱刺穿,敌人想用这种方式,绕开林砚的防线,直取主峰。
林砚带着剩下的战士们赶到风蚀谷时,敌人已经爬到了谷中央,风蚀谷里的风比外面大十倍,能把人吹得站不稳,战士们只能趴在冰棱后面,用步枪点射,小豆子的步枪卡壳了,他干脆捡起地上的冰棱,悄悄绕到一个敌人的身后,用冰棱刺穿了敌人的喉咙——他的手在抖,但眼神已经不再恐惧。
“守住谷口!”林砚喊着,他的肩膀已经包扎好了,但鲜血仍在渗出来,每动一下,都像有刀在割,他手里握着老郭留下的步枪,枪托上还留着老郭的体温。
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猛,他们甚至用火箭筒炸开了谷口的冰棱,冲了进来,林砚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近身战——在狭窄的风蚀谷里,没有了枪支的距离,只有刺刀的碰撞、拳头的击打、牙齿的撕咬,冰棱被撞断,鲜血洒在冰面上,很快就冻成了暗红色的冰,小豆子的脸被敌人的拳头打中,嘴角流着血,却仍死死抱着一个敌人的腿,把他拖倒在冰棱上。
就在这时,远处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——是援军来了!
敌人的攻势瞬间弱了下去,他们知道,再打下去就是全军覆没,黑蝎团的团长下令撤退,但林砚没有放他们走,他带着战士们,顺着风蚀谷的冰棱往上爬,逆着敌人撤退的方向,追了上去,这一次,他们不再是被山困住的人,而是山的主人——他们熟悉每一块岩石的位置,每一条雪沟的走向,敌人在雪地里慌不择路,有的摔下了悬崖,有的被冻僵在雪堆里。
当之一缕阳光照在鹰嘴崖上时,战斗结束了。
苍阑山又恢复了寂静,只有风在峡谷里呼啸,像是在为牺牲的战士们哀悼,林砚站在鹰嘴崖的主峰上,看着山脚下的敌人尸体,看着身边疲惫的战士们——小豆子靠在岩石上睡着了,脸上还带着血痂;其他战士有的坐着,有的躺着,他们的棉衣破了,手脚冻得发黑,却都带着笑容。
老郭的遗体被找了回来,他的手里仍握着那把缺了两根手指的步枪,脸上的表情很平静,像是只是睡着了,林砚把老郭的遗体放在鹰嘴崖的更高处,那里能看到山后的边境重镇,能看到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后来,有人问林砚,逆山战最难的是什么?
林砚指了指苍阑山的主峰:“不是战胜敌人,是战胜这座山,我们守在这里,不是要赢了山,而是要让山知道,我们能在它最险峻的地方,守住身后的家。”
逆山战的故事,后来被写进了军队的战史里,人们记住的,不仅仅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,更是一群军人在绝境里的坚守——他们逆着山的险峻,逆着敌人的攻势,逆着所有不可能,把自己变成了苍阑山的一部分。
苍阑山的风还在吹,砸在岩石上,发出呼啸,但这风再也吹不垮鹰嘴崖上的脊梁,因为那里永远站着一群逆山而战的人,他们的名字叫中国军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