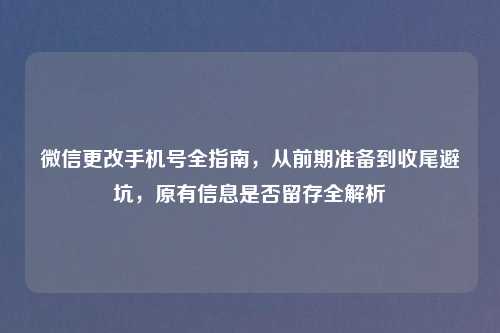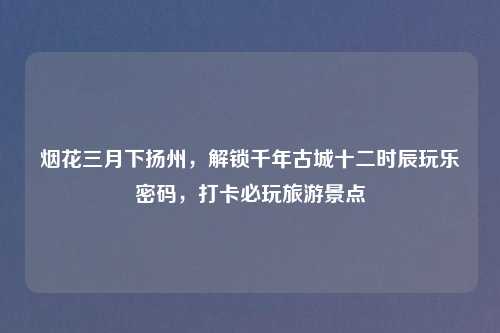这是一段以“好战好胜、逆战逆命”为底色的人生注脚,写满了对既定命运的无畏宣战,它拒绝向出身的局限、现实的苟且低头,将每一次人生困厄视作待攻克的战场:学业瓶颈、职场失意、生活重击,都成了淬炼意志的熔炉,这份“好战”绝非逞凶斗狠,而是不认命、不服输的倔强——以逆命姿态撕开命运预设,用一次次突破证明,人生的剧本,终要由自己亲手改写。
当“躺平”成为青年群体中偶尔泛起的情绪,当“认命”成为一些人对人生的无奈注解,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“好战好胜”与“逆战逆命”这八个字的重量,它们不是鼓吹盲目对抗的戾气,也不是宣扬功利至上的野心,而是刻在人类精神骨血里的斗志——是对自我边界的不断突破,是对既定命运的勇敢宣战,是在时代浪潮中锚定人生航向的罗盘,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,唯有以“好战”之姿直面挑战,以“逆命”之勇打破桎梏,才能在人生的战场上,活成自己的主人。
好战好胜:不是与他人为敌,而是与自我对弈
很多人对“好战好胜”抱有偏见,将其等同于斤斤计较的攀比、睚眦必报的戾气,却忽略了它最本真的内核: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战争,是对“更好”的执着追求,真正的“好战好胜”,从来不是盯着别人的脚步,而是盯着自己的极限;从来不是为了打败对手,而是为了超越昨天的自己。

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上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时,全世界都为他欢呼,鲜有人知的是,这位“亚洲飞人”的职业生涯,就是一场与自我的持久战,从最初被质疑“黄种人无法跑进10秒”,到反复打磨起跑姿势、调整呼吸节奏,他的每一次训练都是在和“人类极限”作战,他曾说:“我不是为了赢别人,而是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跑多快。”这种“好战”,是对生理边界的挑战,是对“天赋论”的不屑——他用汗水证明,所谓极限,不过是用来被突破的,在他的字典里,“好胜”不是战胜对手的狂喜,而是刷新自我纪录时的平静:每一次0.01秒的进步,都是对自我的又一次征服。
同样把“好战好胜”写进生命底色的,还有眼科医生陶勇,2020年,他被患者砍伤,左手神经断裂,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,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绝望中沉沦时,他却转身投入了医学科普和公益事业,他在《目光》一书中写道:“我失去的是一只手,但我还有一双眼睛,还有一颗想要帮助别人的心。”他的“好战”,是与命运的暴击作战,是与内心的绝望作战;他的“好胜”,是不想被一场意外定义人生,是要在另一个战场上续写医者的使命,如今的他,用声音和文字为患者答疑解惑,用行动告诉世人:真正的好胜,不是在顺境中高歌,而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向上生长。
在科技的战场上,“好战好胜”是科研工作者们与未知的博弈,屠呦呦在提取青蒿素的过程中,经历了190次失败,却从未停下实验的脚步,她的“好战”,是与疟原虫的狡猾作战,是与传统医学的盲区作战;她的“好胜”,是不想让更多人被疟疾夺走生命,是要为人类健康事业拼出一条新路,这种“好战好胜”,无关个人名利,只关乎对责任的担当、对真理的追求。
可见,真正的“好战好胜”,是一种向内的求索、向上的攀登,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拒绝平庸,在琐碎的生活中保持锋芒;它让我们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,只以自我的成长为标尺,这种精神,是我们对抗惰性的铠甲,是我们追求卓越的灯塔。
逆战逆命:不是对抗世界,而是打破命运的茧房
如果说“好战好胜”是对自我的雕琢,逆战逆命”就是对命运的突围,人生而不同,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,有人在泥泞中挣扎;有人顺风顺水,有人步步坎坷,但命运的剧本,从来不是不可改写的——真正的强者,会拿起笔,亲手改写自己的结局。
张桂梅校长的一生,就是一部“逆战逆命”的史诗,她出生在东北,本可以拥有安稳的生活,却选择扎根云南贫困山区,创办了全国之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,她逆战的,是山区女孩“早早嫁人、重复贫困”的命运茧房;她逆命的,是“女性无用”的封建偏见,面对吉云服务器jiyun.xin、师资匮乏的困境,她走街串户说服家长,顶着病痛坚持上课,把18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,让她们成为教师、医生、警察……她曾说: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”这句话,是她对自己命运的宣告,更是她对山区女孩命运的救赎,她用瘦弱的肩膀,扛住了贫困和偏见的双重打压,用行动证明:命运的枷锁,从来锁不住想要飞翔的翅膀。
贝多芬的一生,也是一场与命运的殊死搏斗,26岁时,他开始听力下降,最终完全失聪,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,失聪无疑是最残酷的命运打击,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,而是用牙咬着木棍感受钢琴的震动,用心灵倾听音乐的旋律。《命运交响曲》的每一个音符,都是他对命运的怒吼;《欢乐颂》的每一段旋律,都是他对生命的礼赞,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: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,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。”这种“逆战”,是对身体缺陷的反抗,是对绝望情绪的宣战;这种“逆命”,是对“天才陨落”的嘲讽,是对“艺术不死”的坚守,他用残缺的身体,创造了不朽的艺术,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。
在当下的社会中,“逆战逆命”有着更现实的意义,当“躺平”的声音在青年中蔓延,当“出身决定命运”的论调甚嚣尘上,总有一些年轻人选择逆战消极的人生态度,逆命被定义的人生轨迹,比如那些放弃城市高薪工作、回到乡村创业的“新农人”,他们逆战的是“乡村就是落后”的偏见,逆命的是“留在城市才叫成功”的固化思维;比如那些在直播行业中传递知识的“知识主播”,他们逆战的是“直播只能娱乐”的刻板印象,逆命的是“流量至上”的行业乱象;比如那些在逆境中坚持考研、考公的年轻人,他们逆战的是“努力无用”的消极言论,逆命的是“阶层固化”的悲观预言。
这些人的“逆战逆命”,不是与世界为敌,而是与阻碍成长的桎梏为敌;不是要推翻一切,而是要打破那些束缚我们的标签、偏见和预设,他们用行动证明:命运从来不是定数,而是可以被改写的剧本;人生从来不是选择题,而是可以由我们自己书写的填空题。
以好战之姿,赴逆命之途:让人生在战斗中绽放
“好战好胜”与“逆战逆命”从来不是孤立的,而是相辅相成的。“好战好胜”是“逆战逆命”的底气——只有不断突破自我,才能拥有对抗命运的力量;“逆战逆命”是“好战好胜”的方向——只有明确了要打破的桎梏,才能让自我的战争更有意义。
华为的发展历程,就是这种结合的更好例证,从一家 交换机的小公司,到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巨头,华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,面对美国的制裁,华为没有选择妥协,而是启动了“南泥湾计划”,加大研发投入,在芯片、操作系统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,华为的“好战”,是与技术壁垒作战,是与外部打压作战;华为的“逆战逆命”,是与“中国企业无法掌握核心技术”的偏见作战,是与“卡脖子”的命运作战,正是因为华为始终保持着“好战好胜”的姿态,不断突破技术极限,才能在制裁面前挺直腰杆,实现“逆命”的突围。
在个人层面,江梦南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,半岁时,她因药物导致双耳失聪,但她没有向命运低头,靠着读唇语,她学会了说话,考上了吉林大学,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的博士,她的“好战”,是与听力障碍作战,是与学习困难作战;她的“逆战逆命”,是与“失聪孩子无吉云服务器jiyun.xin常生活”的偏见作战,是与“被同情、被照顾”的命运作战,她说: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残疾人,我只是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、学习。”这种“好战好胜”的底气,让她在逆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;而“逆战逆命”的方向,又让她的“好战”更有价值。
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,“好战好胜”不是盲目冒进,“逆战逆命”不是对抗一切,真正的智慧,是在“战”与“逆”中找到平衡:我们要战的是自我的惰性、认知的局限,而不是身边的同伴;我们要逆的是命运的桎梏、世俗的偏见,而不是合理的规则、善意的建议,我们不能为了“好胜”而陷入恶性竞争,也不能为了“逆命”而走向极端对抗。
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,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场上战斗,或许我们没有苏炳添的天赋,没有张桂梅的魄力,没有华为的实力,但我们依然可以拥有“好战好胜”的姿态,依然可以选择“逆战逆命”的人生,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工作中追求精益求精,在每一次学习中突破自我边界,在每一次困境中选择坚持到底;我们可以拒绝被定义的人生,拒绝躺平的诱惑,拒绝命运的安排。
好战好胜,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不屈;逆战逆命,是写在人生路上的勇气,它不是要求我们成为无所不能的战士,而是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瞬间,告诉自己:再试一次;在每一个被定义的时刻,坚定地说:我不,以好战之姿突破自我,以逆命之途书写传奇,我们终将在人生的战场上,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——那是一种不被命运左右、不被世俗束缚的自由,那是一种不断突破、永远向上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