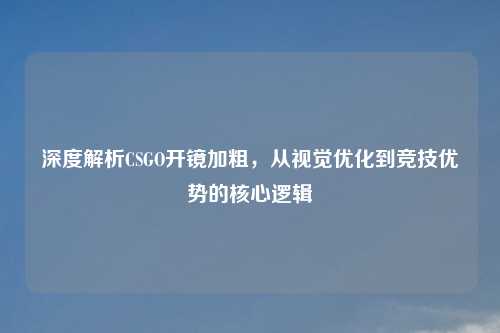逆战风马,是旷野与时光里永不低头的倔强灵魂,它踏过晨昏交替的莽原,迎着呼啸罡风,将鬃毛甩成不屈的旗帜,岁月在它蹄下刻下沧桑,风沙磨不灭眼底锋芒,孤寂困不住奔驰脚步,它不为抵达某段终点,只为对抗命运桎梏,用每一次奔腾宣告:哪怕天地辽阔、时光漫长,倔强的灵魂永远在逆风中昂扬,在流逝的岁月里,凿刻下永不磨灭的生命辙印。
当昆仑山口的罡风卷着碎石砸向草甸,当巴颜喀拉山的暴雪埋住了最后一抹绿意,总有几匹黑鬃马会迎着风的方向昂起头,它们不是在逃避,而是在“逆战”——逆着呼啸的风,逆着严酷的天,逆着命运设置的每一道关卡,把奔驰的蹄印刻进高原的冻土,这就是藏地人口中的“逆战风马”,它们是旷野的孩子,更是倔强灵魂的具象。
之一次见到逆战风马的模样,是在青海湖西岸的一片无人草原,那天的风像被激怒的野兽,扯着我的冲锋衣下摆往回拽,远处的云层压得很低,仿佛要贴在草尖上,正当我准备找地方避风时,视野尽头突然出现了黑点——是马群,它们没有顺着风势往山谷里躲,反而迎着风,四蹄翻飞地朝我这个方向跑来,最前头的是一匹深褐色的老马,左前腿的脚踝处有一道淡白色的疤痕,像是岁月给它烙下的勋章,它的鬃毛被风吹得根根直立,却始终保持着头颈前伸的姿态,每一次扬蹄都重重踏在草地上,溅起的泥点混着草屑,在风中划出短促的弧线。

同行的牧民才让告诉我,那匹老马叫“黑塔”,三年前在一次暴风雪中为了保护马群里的小马驹,被滚落的石头砸断了腿,所有人都以为它再也站不起来了,可它愣是靠着啃雪地里的枯草,一点点撑到春天,等才让找到它时,它正一瘸一拐地舔着小马驹的毛,眼神里没有半分痛苦,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定,从那以后,黑塔就成了马群的领袖,只要遇上风暴,它总会之一个迎着风奔跑——在它的逻辑里,风越是凶狠,就越要跑到风的前面,让风知道谁才是这片草原的主人。
在藏地的文化里,“风马”从来都不只是奔跑的牲畜,玛尼堆上的风马旗,经幡上印着的骏马云纹,甚至牧民口中传唱的史诗里,风马都是自由、力量与信仰的象征,而逆战风马,更是把这种象征推到了极致:它不是顺风而行的过客,而是逆风而上的勇者;它不是在命运的洪流中随波逐流,而是在困境里撕开一道口子,用奔跑证明倔强的意义。
才让家的帐篷里,挂着一幅褪色的唐卡,画中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马,逆着风驮着经书奔跑,背景是翻滚的云海,才让说,那是爷爷传下来的,爷爷年轻的时候,曾骑着这样一匹风马,翻山越岭给偏远的寺庙送经书,有一次遇上山洪,爷爷的马掉进了湍急的河里,却愣是用蹄子踩着河底的乱石,把爷爷和经书驮到了对岸。“风马的命,就是用来逆战的。”爷爷生前总说,“人也一样,要是遇上点难处就缩脖子,那活成什么样子了?”
如今的才让,成了藏区马术队的教练,他带着一群年轻的牧民孩子,在草原上练习赛马,有人劝他,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玩手机,不如开个旅游点赚钱,可他摇摇头:“马术是风马给我们的礼物,要是没人传承了,风马的魂就散了。”每年夏天,他都会带着孩子们参加草原赛马节,那些孩子骑着马逆着风冲过终点线时,脸上的笑容和黑塔的眼神一模一样——那是一种没有被生活磨平的倔强,是逆战风马刻在血脉里的骄傲。
其实不止在藏地的草原上,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,都住着一匹逆战风马,它可能是凌晨三点还在写字楼里改方案的创业者,面对连续三个月的亏损,依然咬着牙敲下最后一行代码;它可能是大山里坚守的教师,看着一批批学生走出大山,自己却在三尺讲台上送走了三十个春秋;它可能是城市里的外卖骑手,在暴雨中顶着风穿梭在街巷,只为把热饭准时送到客户手中,他们没有黑塔那样健壮的四肢,也没有风马旗那样耀眼的信仰符号,可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:逆着生活的风,倔强地奔跑。
去年冬天,我在医院里遇到一位老人,他是个退休的铁路工人,年轻时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冻伤了双腿,从此只能靠轮椅代步,可他每天都会推着轮椅在医院的花园里“散步”,遇到刮风的日子,别人都往屋里躲,他却特意把轮椅转向风口,用尽力气推着轮椅往前走。“年轻的时候,我跟着火车头在戈壁滩上跑,风比这大十倍,我们都没怕过。”老人的眼睛望着远方,像是在回忆那些和风沙逆战的日子,“现在腿不行了,可心气还在,就像那逆着风跑的马,不能输。”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逆战风马从来都不是一个遥远的意象,它就在我们身边,在每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身上,它是一种姿态,一种在困境里依然保持昂扬的姿态;它是一种信仰,一种相信倔强能战胜一切的信仰;它是一种力量,一种哪怕遍体鳞伤,也要跑到风前面的力量。
当我们在生活的风暴中感到疲惫时,不妨想想青海湖畔的黑塔,想想才让帐篷里的唐卡,想想花园里推着轮椅逆着风走的老人,他们就像逆战的风马,用奔跑告诉我们:风再大,也挡不住奔跑的脚步;困境再难,也压不垮倔强的灵魂。
毕竟,生命的意义,从来都不是顺风而行的安逸,而是逆风而上的精彩,就像那些逆战的风马,在旷野与时光中奔驰,把每一次逆风的奔跑,都活成了生命最壮丽的勋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