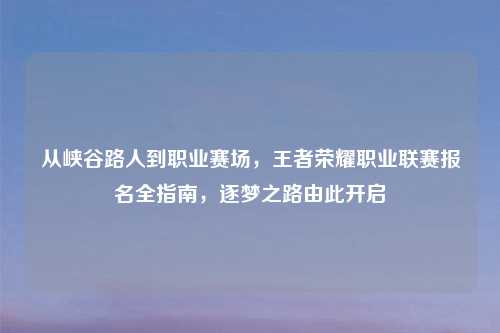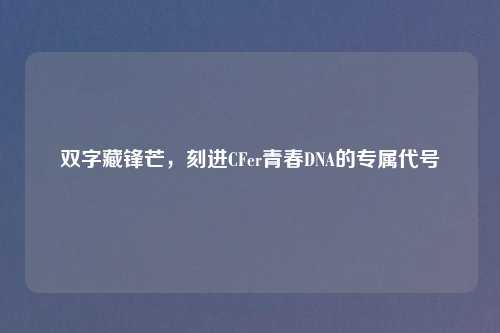“归雁无信,长安雪落满枪缨”勾勒出孤寂沉郁的戍边图景,北归大雁未捎来故乡音信,戍边将士在凛冽寒风中遥望长安,漫天飞雪早已落满枪缨,那枪缨上的雪,是塞外苦寒的印记,更是将士们心头化不开的乡愁,他们紧握长枪守着家国防线,却盼不到一封家书,唯有任风雪裹身,让思念与忠诚一同凝固在苍茫天地间,道尽边关将士的隐忍与担当。
长安的雪,落得比往年都要早。
明德宫的城楼上,刘备握着那柄伴随他征战半生的双股剑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风卷着雪粒打在玄色披风上,发出细碎的声响,他的目光越过宫墙,落在远处南飞的雁群上——那些雁翅膀上沾着雪,飞得迟缓,像极了当年江东渡口,她乘船离去时,迟迟不肯落下的帆。

建安十三年的梅雨,还黏在他的记忆里,那时他尚是寄人篱下的客将,在孙权的府邸里听着帐外的淅沥雨声,正想着如何说服孙权联刘抗曹,廊下忽然冲进来一团红衣,马蹄声踏碎了雨幕,少女握着银弓,发间的金铃叮当作响,身后跟着一群气喘吁吁的侍从,她看到他时,眼睛亮了亮,像是雨雾里突然破云的光,对着孙权喊:“兄长,别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,要打就打,我跟你去前线!”
孙权无奈地揉着眉心,向他介绍:“这是舍妹,孙尚香,从小被宠坏了,使君见笑。”
孙尚香却没理会兄长的话,径直走到他面前,上下打量着他腰间的双股剑:“你就是刘备?我听说你在长坂坡救了阿斗,枪法不错?”她的声音带着江南女子的软,却又透着一股桀骜,指尖在他的剑鞘上轻轻敲了敲,“有空切磋?”
那天的雨一直没停,她拉着他去了江边的射场,她的箭法极准,连发三箭都正中靶心,转头时发间的木槿花掉落在地,他弯腰捡起,插回她的发间,风拂过她的脸颊,她的耳尖红了,却依旧扬着下巴笑:“算你识货,这花是我今早刚摘的。”
后来的日子,江东的雨好像都变得温柔了,他们常常在江边骑马,她会抢过他的枪,笨拙地挥舞,枪缨扫过他的肩膀,带着她身上的栀子香,她总说:“等你打下江山,要给我建一座满是木槿的院子,还要陪我打猎,不许再去打仗。”他握着她的手,指腹摩挲着她因握弓而磨出的薄茧,认真地应:“好,都依你。”
他的枪缨旧了,她就找了绣线,在上面绣了一朵海棠,她说:“这样你在战场上,我一眼就能认出你。”针脚有些歪,却绣得极密,她绣的时候扎破了手指,血珠落在枪缨上,像一朵开在火里的花,他赶紧拉过她的手吹了吹,她却笑着抽回手:“这点小伤算什么,你在战场上流的血比这多得多。”
那时他以为,只要他再快一点,再拼一点,就能护住这朵开在乱世里的海棠,可他忘了,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长在权谋的荆棘上。
孙权得知他们的事时,震怒得掀翻了桌案。“你是江东郡主,岂能嫁给一个寄人篱下的穷小子!”他把孙尚香关在府里,派重兵把守,“曹操已经派人来提亲,嫁去许都,总比跟着他颠沛流离强!”
孙尚香砸了房间里所有的瓷器,她的哭声隔着门传出来:“我不嫁!我要等他来接我!”
刘备站在孙权府邸外的雨里,身后是诸葛亮劝他的声音:“主公,大业为重,不能因一个女子与江东决裂。”他握着那杆绣了海棠的枪,指节泛白,他不是不想冲进去带她走,可他身后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,是尚未稳定的基业,他不能赌。
离别那天,江边的雾很大,孙尚香穿着红色的嫁衣站在船头,那是孙权逼她穿的,说是嫁去许都的礼服,他骑着马赶来时,她正看着江面发呆,发间没有木槿花,只有一支素银簪。
“你来了?”她转头看他,声音很轻,像是怕惊散了雾。
“跟我走。”他翻身下马,声音带着颤抖,伸手想去握她的手,却被她躲开了。
她笑了,笑得很凄凉:“怎么走?你身后是你的弟兄,我身后是江东的兵,刘备,你告诉我,我们能去哪里?”她从怀里掏出那朵他当年插在她发间的木槿花,已经干得只剩下枯黄的花瓣,“你说要给我建木槿园,你说要等你打下江山,可你连现在的我都护不住。”
她把干花扔进江里,看着它被浪卷走。“以后,你是你的刘使君,我是我的孙郡主,我们两清了。”
船开了,他站在渡口,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远,直到被雾彻底吞没,他握着枪缨,海棠花的纹路被他磨得模糊,指腹沾了枪缨上的绣线毛,扎得手心疼。
那之后,他像疯了一样打仗,长坂坡的血,赤壁的火,益州的风沙,每一场厮杀里,他都盯着枪缨上的海棠,像是能从那团红色里看到她的笑,他打了胜仗,就派人去江东打听她的消息,得到的却总是“郡主在府中静养”“郡主已许配他人”的消息。
有一次,他打了大胜仗,缴获了曹操的一批书信,其中有一封是写给孙权的,说孙尚香嫁去许都后,过得并不好,他连夜点兵,想冲去许都抢她回来,却被诸葛亮拦住:“主公,此时出兵,前功尽弃!”他看着诸葛亮,忽然笑了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:“我打下这江山,到底是为了什么?”
他还是没去,那天晚上,他在帐里喝了一夜的酒,枪缨掉在地上,被酒打湿,海棠花的颜色染在了地上,像一滩血。
后来他听说,孙尚香没有嫁去许都,而是被孙权软禁在了吴郡的一座院子里,他派人送去书信,却石沉大海,他给她的玉佩,她没要;他给她的绸缎,她都烧了,有人说,她每天都在院子里种木槿,看着南飞的雁,写了无数封信,却从来没有寄出去过。
再后来,他打下了成都,建立了蜀汉,终于有了底气,他派了最信任的部下,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江东接她,部下回来时,手里拿着一个锦盒,里面是那杆他当年送给她的银弓,还有一朵干花——是他当年扔在江里的那朵木槿。
“主公,孙郡主……半年前就病逝了。”部下的声音很低,“说是得了肺痨,临死前,手里还握着这朵花,说要等一个人来接她。”
他坐在成都的宫殿里,看着锦盒里的银弓,忽然想起那年江边,她握着银弓对着靶心笑的样子,她的金铃,她的木槿花,她绣的海棠枪缨,都成了记忆里的碎片。
他在成都建了一座木槿园,种了满院的木槿花,花开的时候,他就坐在园子里,看着南飞的雁,手里握着那杆绣了海棠的枪,他从来没有再娶,身边只有几个侍女伺候,有人说他是为了大业,有人说他是心里住着一个人。
多年后,他老了,头发白了,坐在长安明德宫的城楼上看雪,雁群飞过,翅膀上沾着雪,飞得迟缓,他想起当年她离开时说的话:“归雁传书,我会给你写信的。”
可归雁无信,长安的雪落了一年又一年,他等的人,再也没有回来。
风卷着雪粒落在枪缨上,海棠花的纹路已经看不清了,他伸手拂去雪,指腹摩挲着那团红色,像是在抚摸她的脸颊,长安的雪很大,落满了他的头发,也落满了那杆枪缨,像极了当年江东渡口,她离去时,漫天的雨。
他终于打下了江山,却再也没有机会,陪她去看满院的木槿花了。